(一)、保證期間既不是訴訟時效期間,也不是除斥期間
關于保證期間和訴訟時效的問題很亂。因為最高人民法院在這個問題的意見上就曾先后變化,最高人民法院曾經認為保證期間就是除斥期間,也曾認為保證期間是訴訟時效期間,但我認為這兩個意見都是不對。
其一,保證期間不是訴訟時效,道理跟方才類似。首先,保證期間消滅的是保證人的債務實體,消滅的是債權人請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實體權利,而訴訟時效不消滅實體權利,只是不能請求或抗辯權產生。
其二,保證期間,保證人還有解除合同的權利,所以它涉及的也不僅是普通的債務,它也還有權利上的問題,而訴訟時效是沒有這個特性的。
其三,兩者的起算不同。保證期間,當然是有約定的就按約定起算,沒有約定的,根據《擔保法》規定,就從主債務履行期屆滿之日起算六個月。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又增加了新的內容,將擔保法的六個月改為了兩年。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原來的六個月規定是針對那些根本怠于行使權利(躺在床上睡眠)的人來說的,但是現在的債權人總是積極的、想辦法要把保證人套住,比如在借款保證合同中常常約定保證責任一直到還清本息、全部債務履行完畢之日止。這說明了銀行的法律意識還是很濃厚的,它的目的無非是把保證人永遠捆在里面。最高人民法院因而認為債權人沒有怠于行使權利,那么就要優惠一點,所以就規定保證責任期間不是從主債務履行期屆滿之日起六個月了,而要從主債務履行期屆滿之日起兩年(這是我親自問他們最高人民法院的,我問“你們憑什么要改《擔保法》的六個月為兩年呢?”,他們的理由就是上面所說的)。而訴訟時效不是這樣起算的,它是權利人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之日起兩年內。起算不同,正因為起算不同,你將其視為是訴訟時效是不行的。其四,保證期間,債權人主張了,保證期間功成身退,訴訟時效制度取而代之,如果訴訟時效制度還有這個權利,保證期間制度還要來干什么呢?
2、保證期間也不是除斥期間。
除斥期間針對的是形成權,我方才說了,保證期間針對的主要是債權債務,針對的是保證人向債權人履行保證債務。再者,除斥期間不存在轉化成訴訟時效期間的問題,因此,將保證期間視為除斥期間也不對。其三、除斥期間的起算在我國是形形式式的,比如《合同法》第55條規定的起算是從撤銷人知道權利被侵害開始,《合同法》第47條、48條規定的起算是從催告確定的一個日期開始。其四、除斥期間原則上是法定,而保證期間很多情況下是約定(當然了,《合同法》第95條規定的除斥期間是約定,這是中國特色,境外的法律沒有這樣規定)。所以,我認為保證期間和訴訟時效期間、除斥期間是不一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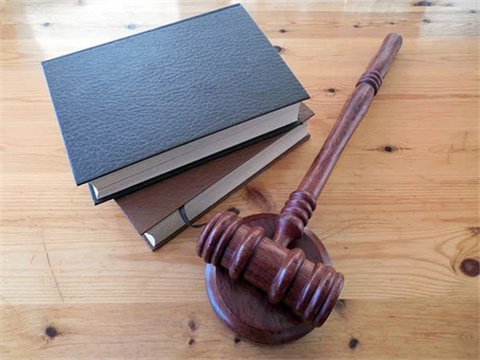
(二)連帶保證責任和一般保證責任
1、連帶保證責任連帶責任保證
由于保證人沒有先訴抗辯權,那么從主債務履行期屆滿,如主債務人違約,那么實際上主債務的訴訟時效就是從主債務履行期屆滿的日開始起算,我個人認為,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也開始起算。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我先后有一個變化過程,我原來認為在連帶責任保證中,主債務人的債務與連帶責任的保證人的保證債務是同一個債務,只不過是由主債務人和連帶保證人連帶承擔,那么解釋訴訟時效的中斷和中止都很容易、很方便:只要主債權人向主債務人或保證人任何一個主張即可。可是在后來的討論過程中,我這個觀點顯得非常孤立,有人說,保證債務是通過保證合同產生的,而主債務是通過借款合同等主合同產生的,它們產生的法律行為都不同,又怎能認為它們是同一個債務呢?(同一個債務它應該從同一個地方生出來呀)。我覺得他們說的有道理,后來我就放棄了自己原來的觀點。我現在的觀點是,即便在連帶責任保證中,主債務是一個獨立的債務,保證債務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債務,只不過保證債務具有從屬性,要跟著主債務的情況來變化。但是這個觀點不影響主債權人向主債務人主張,在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的時候,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也跟著中斷。當然,如果債權人直接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毫無疑問肯定中斷。
(2)、一般保證責任關于一般保證責任的問題就更大了。當然了,我如果作為仲裁員來裁決案件,肯定是要以《擔保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司法解釋為裁決依據。可我現在是作為一個教授的身份,我就可以對相關立法提出批評意見,這屬于立法論。(角色不同,對法律的解釋也不一樣)。作為一個教授身份,我對《擔保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都提出過批評意見。《擔保法》規定,在一般保證責任中,債權人向主債務人起訴或者申請仲裁,那么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中斷。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認識到《擔保法》的上述規定錯了,因為我們私下討論過并提出疑問,最高人民法院也承認《擔保法》的上述規定不對,但現行的司法解釋也就只好將錯就錯了(這話不是公開的,不具有法律效力)。
《擔保法》規定的是“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中斷”,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將其改為“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開始起算”,它由《擔保法》的“中斷”改為“起算”是一個進步,但是即使如此,我也仍然認為是不對的。理由如下,其一、一般保證債務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就是保證人的先訴抗辯權。那么先訴抗辯權什么時候行使呢?如果主債務人根本沒有違約,保證人對債權人的抗辯不是先訴抗辯,而是債務履行期沒有截止的抗辯。其二,主債務的履行期截止了,主債務人沒有履行主債務而構成違約,這時候,保證人就不能以履行期未截止進行抗辯了,而必須用先訴抗辯,他可以主張債權人應該先找債務人,而不能直接找我一般保證人。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債權人是否能夠以“我已經找了主債務人,但他已經違約了,所以我要求你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進行反抗辯呢?我認為這樣的抗辯是不行的。因為《擔保法》里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定,債權人要向一般保證人主張其承擔保證債務,必須是就“主債務人的財產強制執行而不能履行債務”,只有這個結果出現,債權人才能要求一般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如果這個結果不出現,債權人就主張一般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保證人仍然能行使先訴抗辯權,將債權人抗辯回去,而不承擔保證責任。
羅南刑辯律師認為,《擔保法》中關于“強制執行主債務人的財產而不能履行債務”的說法不對,第一,“不能履行”在這里用的詞不對。因為“不能履行”它有特定的涵義,它是指如果履行標的物是特定物的時候,特定物毀損和滅失了,不可能交付的了,這叫做“不能履行”;如果是以行為作為履行標的的,比如要提供行為(服務)的人死亡了,這人喪失了行為能力,喪失了實際的服務能力,那么可以認為這人“不能履行”;如果履行的標的物是種類物,除非所有種類物全部毀損滅失,原則上不能叫“不能履行”;金錢債務不存在不能履行的情況。大家想想,我們的保證大部分是用在借款合同中的,借款合同的標的物恰恰是金錢,沒有不能履行的可能,那法條上還規定什么“就借款人財產強制執行不能履行”呢?金錢債務是沒有不能履行的,這個“不能履行”永遠出現不了,這也意味著一般保證人永遠也不會承擔保證債務,只是買一個好名。從上述條文的文義解釋是這樣的,當然,文義解釋得服從目的解釋,該法條原本的立法目的并不是我方才所作的文義解釋那樣,它的立法目的是當債權人申請了強制執行主債務人的財產不奏效,那么債權人就可以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比如說,主債務人可能財產很多,但是他把財產轉移到了玻利維亞,因為我國與玻利維亞沒有司法協助,強制執行不了;又或者主債務人已經將財產深埋地下或通過其他途徑使債權人無法得到,這就叫做“不能奏效”。這時,債權人就可以找保證人要求承擔保證責任,債權人不能行使先訴抗辯權,而要承擔保證責任.所以,我認為《擔保法》的上述規定應改為債權人就主債務人的財產強制執行而“沒有效果”,而不要用“不能履行”。
只要強制執行主債務人沒有效果,就可以找保證人,保證人就不能行使先訴抗辯權,就要承擔保證責任。此外,我認為,根據前述給付義務適用訴訟時效的法理,一般保證債務不是原給付義務,而是給付義務,那么保證人沒有違約,憑什么適用訴訟時效呢?所以這時候的訴訟時效只能從債權人請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保證人沒有理由再拒絕的時候開始起算。這個時間比主債務人的違約還要滯后一段時間,因此《擔保法》關于“一主張就中斷”的說法不對。訴訟時效根本就沒開始,又談何中斷呢?同樣,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關于“一主張訴訟時效就開始起算”的說法也不對,因為債權人主張了后還要過一段時間,在判決、裁決生效后強制執行了沒有效果,才開始起算訴訟時效。關于上述問題,羅南刑辯律師是這樣來考慮的。當然,我再重申一遍,我的上述觀點是立法論,是我關于法律應該怎樣規定的意見,作為律師、法官、仲裁員,我們還是得按照現行法的規定來做。現在民法典草案在這個問題上也正在往這個合理的、正確的方向改,但是還是不理想,因為,老實說,在保證里面的問題還是很多的。五、關于違約金的問題。深圳因為處在經濟發達的地區,反映的案件問題也多,這是個好事,因為這些案件反映的問題大都是我們現行法上沒規定的,這些問題促使我們進行法律思考,來研究有用的理論。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經濟合同法適用問題的若干意見的規定》被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經濟合同法適用問題的解答》明文廢止并取代了,我對這個印象很深,因為我過去在打官司的時候,對方律師恰恰引用1984年的上述規定,這里提一下,由于我們現行《合同法》已經廢止了《經濟合同法》,按邏輯來講,上述的司法解釋是根據《經濟合同法》來做的,所以也不應該再有效了,不過這個案件如果是發生在過去的案件,那么還是有用的。我現在說一下原來合同法上關于違約金的規定,拋開涉外經濟合同法,就談國內合同法部分,包括《經濟合同法》及相關條例、細則、司法解釋等等。
(一)、違約金是最低數額的損害賠償。
在合同履行過程中,一方違約了,違約方要賠償守約方的經濟損失。如果合同中有違約金的約定,違約方是一定要賠償守約方該約定的違約金的,如果違約方賠償了該違約金以后,還不足彌補守約方的損失,那么,違約方仍須繼續賠償守約方損失,所以說違約金是一個最低數額的損失賠償。違約金是守約方最低能得到的最低賠償數額,如果守約方還能舉出證據來證明違約金低于實際損失,還能得到更多的賠償。這是原來《經濟合同法》的規定,這樣的規定的優點是對守約方的損失額的補償比較有保證。(如果守約方損失額低,可違約金高,這樣我守約方就有賺了。尤其是在經濟合同法里,約定的違約金數額一般是不減免的,只有在違約方經濟非常困難等等好幾個條件下才能免,在實際工作中一般很難采用,所以基本上是不減免的;如果約定的違約金數額低于守約方的實際損失,守約方還可以通過舉證,向違約方追回損失)。
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中也是這樣規定的,在現行《合同法》草案的討論過程中,最高人民法院仍然希望這樣,但是學者都不贊同,認為原來的相關法律中關于違約金的規定有一個不好之處,就是違約方哪怕只是違約一秒也是違約,有人精明,他就開始計算“我違約一秒鐘也要賠給你守約方約定的違約金,違約半年也是違約,也是同樣要賠給守約方約定的違約金。那我干脆就一直這樣違約下去吧”。這樣,我們用俗話說就是不利于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了。這樣的規定確實存在著這樣一個毛病:它鼓勵人們繼續違約下去,因為無論違約輕重都要賠償相同的違約金。
(二)、違約金的性質違約金究竟是懲罰性的還是賠償性的呢?
這在合同訂立的時候看不出來,只有在違約真正發生,并開始計算損失的時候才可以看出來。如果約定的違約金數額高于實際經濟損失數額的,那么它是懲罰性的;如果約定的違約金數額低于實際損失數額的,那么它是賠償性的。所以,這種事后算賬,說違約金是懲罰性的還是賠償性的,就有點文字游戲的意思了,價值不高。所以學者們不同意再用這種方式,這種方式是前蘇聯的,英美的方式和這個類似,但不完全一樣。學者們的意見是現行《合同法》改成德國式的。所謂“德國式”的違約金規定是這樣的,原則上法律不允許合同當事人在合同里規定懲罰另一方的東西,因此,原則上法律也不允許合同當事人預定懲罰性的違約金,所以違約金的性質應該是賠償性的。
賠償性違約金只不過是賠償損失數額的事先估定,這叫“損害賠償額的預定”。這樣規定,是因為德國法律人士從實務中發現,賠償損失的問題容易糾纏不清,尤其是我們所說的“可得利益損失”(在德國,被稱為“所失利益”)。羅南刑辯律師舉例來說,比如守約方說如果我正常營業,我是應該賺這么多錢的,但現在由于你違約方的違約,使我得不到應賺的錢,這就是我的損失。但這一部分損失究竟是多少錢呢?在這個問題上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很難計算出來,就是遇到天才,他也會束手無策。這樣久裁不決的案件不理想。所以能不能找到一個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呢?找到了,這就是賠償性違約金。既然事后計算損失過于麻煩,我們就不要事后計算,我們在訂立合同的時候將該損失確定下來,如果一方違約了就得賠償約定的數額。既然這損失是合同當事人預先估算的,那么在合同一方違約以后,守約方只能在約定的違約金和損失賠償中選擇其一。因為違約金和損失賠償在本質上是一個東西,所以守約方只能要求其中一個,不能要求兩個,如果要了兩個,守約方就獲得了不當得利,就違反了合同法的基本宗旨。可是,德國法同時又設定了例外,在遲延履行的情況下,可以約定一個懲罰性違約金。
說句老實話,到今天為止,我仍然還沒搞明白:為什么在遲延履行的情況下,才允許有懲罰性違約金?它規定在遲延履行的情況下,違約金可以和賠償損失并罰。“遲延履行”是指合同約定有履行期限,履行期限屆滿了,一方沒履行或者雖然履行了,但是不符合要求(這是德國人所說的遲延履行)。舉個例子,如果合同約定違約金為20萬元,在合同履行過程中,一方真的違約了,經計算,違約方給對方造成的損失是10萬元,那么守約方在要求10萬元的損失賠償的同時還可以再要求20萬元的違約金,這時守約方就獲得了超出了合同履行所帶來的利益。德國法對這種現象是允許的,而英美法對這種現象可以不允許。德國法規定,在遲延履行情況下,守約方一方面可以要求違約方繼續履行原來的債務,同時還可以要求違約方支付違約金。
德國學者認為這也是懲罰性違約金的規定。當時我們起草合同法的時候,也將這樣的規定抄了下來形成起草意見,但是到最后,全國人大去掉了上述的第一個意見,不同意守約方一方面可請求違約方支付違約金,另一方面還可以同時要求違約方支付賠償損失。但全國人大保留了上述第二個意見,形成了《合同法》第114條第3款:“當事人就遲延履行約定違約金的,違約方支付違約金后,還應當履行債務”。那么,在日后我們的案件里,關于違約金怎樣確定的問題,我認為首先要看違約金是針對遲延履行的,還是針對遲延履行以外的。如果是針對遲延履行以外的違約行為的,那么這個違約金一定是賠償性違約金,因為法律不允許在這種情況下設定懲罰性違約金,懲罰性違約金的約定無效。這個賠償性違約金就和賠償損失是一個東西,你只能要一個,不能要兩個。如果說有什么不同,只不過違約金是事先估算的,賠償損失是事后計算的。(如果違約金是針對遲延履行的,那么這個違約金是懲罰性違約金。在違約方遲延旅行構成違約的時候,守約方)既要求違約方支付違約金,又有權要求違約方繼續履行。但是我國的現行法不允許債權人要求違約金和損失賠償同時支付。
(三)、違約金與定金關于違約金與定金的關系
現在主要規定在《合同法》的第115條、第116條。原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說定金是擔保,違約金是違約責任,兩個目的功能不同,所以可以并罰。一方違約了,守約方可以同時請求定金和違約金。《合同法》將這一原來的規定改為,定金和違約金這兩個不能并罰,守約方只能選擇其一。這樣一來,如果當違約金、定金的數額都少于實際損失數額的時候,守約方就倒霉了,因為守約方無論請求哪個都不能彌補實際損失。出現這樣一個問題怎么辦?我個人的意見是,在這個時候,守約方可以放棄定金的條款,不主張定金,因為即使請求了也不夠彌補實際損失。守約方應在主張約定的違約金賠償后引用《合同法》114條第2款“約定的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增加;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的規定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把低的違約金增加上來,從而使守約方的損失得到完全的彌補。第二種方法,守約方不主張違約金條款,也不主張定金條款來要求違約方賠償,而是直接引用《合同法》第113條第1款的規定索賠(當然如果能引用該條第2款就更好,因為第2款是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因為,這一條規定的是完全賠償原則,根據該條的規定,守約方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賠償。不過,守約方放棄違約金條款和定金條款,而引用合同法113條第1款的規定,面臨著在理論上意思自治原則和法定規定的沖突(當然,為了打贏官司可以不理),定金條款和違約金條款是合同當事人約定、意思自治的表現,怎么合同一方就扔在一邊,轉而引用法定的賠償來索賠呢?這樣怎么來擺意思自治的地位呢?這種方法面臨著這樣一個挑戰。我查看了美國的判例,關于能否撇開約定而引用法定進行索賠的問題,有的判例認為行,有的判例不行。這個問題在中國在理論上應該怎樣來回答,還需要研究。
(四)、委托合同的違約賠償問題
有一位先生談到,如果是委托代理合同(羅南刑辯律師準確的說是委托合同代理關系,委托和代理是兩回事,代理是三者關系,委托是兩方關系),因《合同法》規定,對這種合同,當事人都可以隨時解除合同,但合同解除以后,有責任的一方應該承擔賠償損失的責任。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委托人沒有支付代理費,代理人是否有權要求?如果給了,又能否保持住呢?這里面就涉及到賠償數額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如果是委托方違約,他沒有任何正當理由要求解除委托,只是說不想讓代理人幫他辦了,而代理人又是完全合法正當的,代理人當然有權留住所收取的代理費(這個費用即使被看成是代理人將來要取得的預期利益或可得利益,也是沒有問題的)。如果是代理人提出解除合同無正當理由,我認為,就應該來算帳,算一算代理人干的期間,委托人應該支付多少錢。請注意,這里用的是“應該”,不是“一定”,因為委托人委托的事情沒辦成,委托人不見得要支付代理人這么多的錢。
《合同法》第52條有個規定,雙方當事人的合同違法,需要解除,如果合同雙方當事人都不主張,合同以外的其他人是否有權提起訴訟要求解除他人的合同?有這么一個案件,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的,雙方當事人簽訂一個合同,那么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認為這合同違法,他援引《合同法》第52條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解除他們兩人之間的合同關系,那么他與合同沒有直接利害關系,他只是與合同的一方當事人有點債權債務關系,但是他起訴時并沒有援引其他條款,只是說這合同違法了,是無效的,請求法院解除他們的合同,除此外,他沒有別的要求,法院也受理而且還開庭審理了。我們覺得他是否有權要求通過訴訟方式解除與他沒有利害關系而且其理由還是認為他們的合同違法,是這么一個案件。[崔教授]:這個問題如果是適用《合同法》第52條的話,這合同應該叫做“確認無效”,而不應該叫做“解除”,解除是《合同法》第93條、94條條文。關于不是合同當事人的其他人能否請求法院確認合同無效,從理論上,從我個人意見說應該是可以的,因為無效是絕對的無效,自始無效,任何人都可以主張的無效,你只是一個主張而已,并不能發生法律效果,真正發生法律效果的是由法院來作出,法院是在行使國家權利,用通俗的話說,你只不過在舉報罷了,從原理上也應該這樣理解。在這里,羅南刑辯律師說一個真實的故事,我的師弟當時在國有資產管理局,在國有資產查處司,他希望我在《合同法》草案討論的會上提出來,當他們發現國有資產在通過訂合同流失的時候,他們也有權起訴,請求法院確認那個合同無效,保住國有資產。











 網站首頁
網站首頁  在線咨詢
在線咨詢  電話咨詢
電話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