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誹謗案件中,他人的“點擊”行為在誹謗罪與傳播淫穢物品罪中的意義,從表面上看似具有相同,實則不然。首先,“他人”在誹謗罪與傳播淫穢物品罪中屬于自己不同的范疇。上海刑事律師就來為您講解一下相關的情況。

傳播淫穢物品罪是侵犯中國社會法益的犯罪,客體為社會資本主義思想道德教育風尚,而良好職業道德文化風尚的承載企業主體作用即為一個社會發展民眾,因此,點擊淫穢電子數據信息技術的人認為應該可以歸類于被害人群體,雖然通過點擊者出于自愿但是其身心全面健康問題無疑遭受了侵犯(或是一種潛在侵犯)。
與之不同的是,在誹謗罪中的實施“點擊”、“瀏覽”與“轉發”的行為人則完全不屬于被害人群體,屬于他們無關的第三者。其次,基于前述分析原因,在傳播淫穢物品罪中“點擊量”是屬于經濟犯罪研究結果的范疇,結果當然也是屬于這個情節的內容。
但是在誹謗罪中他人的點擊次數或是轉發次數已經不能有效表征被害者被誹謗的狀態,不能實現歸屬于犯罪調查結果的范疇,也不應只是作為主要情節更加嚴重存在與否的標準。
以他人的轉發和其他行為作為定罪標準,違反責任原則。問責制原則中的個人責任要求“只能對行為人的個人行為進行批評”。即使在共同犯罪中,有組織犯罪也因為對他人的犯罪行為具有因果力,對他人的行為有促成作用,所以對其組織的他人的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但是,行為人不能對他人超出其控制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這是 "責任與行為并存 "的要求
根據解釋,數量標準是相同的誹謗信息被點擊、瀏覽和轉發的次數。也就是說,規定的點擊和瀏覽誹謗信息的“5000次”,不僅包括犯罪人在發布誹謗信息后點擊和瀏覽的次數,還包括第三人轉發該信息,然后由他人點擊、瀏覽的次數。顯然,其他人的轉發和其他行為為演員的捏造,釋放犯罪的“重量”增加了重量。
即使誹謗性信息被他人“點擊”、“瀏覽”或“轉發”的狀態被認為是危害后果,行為人也不應承擔全部責任,尤其是刑事責任。首先,網絡服務平臺提供者的疏忽對誹謗信息的傳播和擴散審查不嚴負有責任。“谷歌搜索引擎(技術專家稱之為算術程序)的原理體現了‘大眾的智慧’。換句話說,點擊一條信息的人越多,這條信息就越有可能呈現給后來的搜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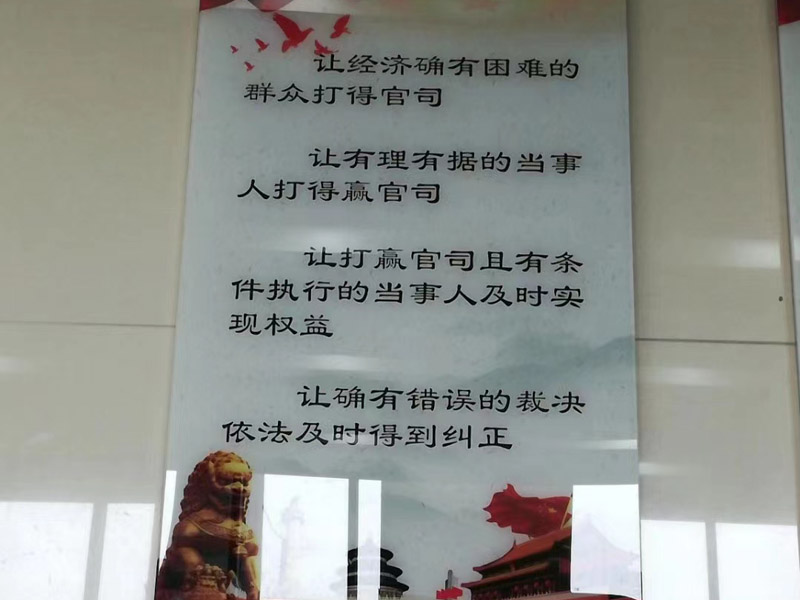
換句話說,網絡搜索引擎依賴的是網民對熱門信息條目的點擊率,而不是信息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可以說,互聯網提供商并不知道肇事者發布的誹謗信息是為他們編造的。但是,退一步說,即使供應商認為行為人發布的信息是真實信息,有些信息也是不應該傳播的。
比如行為人誹謗某人婚外包養小三,即使信息屬實,在網上公開公布也是對當事人名譽的侮辱或者對他人隱私的侵犯,供應商有義務禁止此類信息在網上傳播。其次,網民不負責任的“轉發”也助長了誹謗信息的傳播。
網絡上充斥著各種不明不白、未經核實的信息,網民心知肚明。他們雖然不知道信息是誹謗性的,但卻不顧信息的真假,盲目地、不負責任地 "圍觀 "和 "轉發 ",客觀上無法超脫于危害后果的發生和擴大。所以這種情況完全以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而告終,涉嫌違反問責,公眾難以接受。

上海刑事律師想說的是,如果說上述案件中的第三人因為不知道誹謗信息是出版人捏造的,并沒有故意主觀誹謗,而是客觀上在傳播誹謗信息中起到了“幫助”的作用,那么,如果誹謗信息的傳播和傳播是出版人的責任,那么第三人即使知道誹謗信息是出版人捏造的,也應當重新傳播和傳播誹謗信息,解釋的規定完全不符合責任原則的要求。











 網站首頁
網站首頁  在線咨詢
在線咨詢  電話咨詢
電話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