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到草案,立法機關終于意識到草案第308-1條單列立法手段所體現的立法歧視問題,如果司法工作人員、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或者其他訴訟參與人在不依法開庭審理的案件中泄露不應公開的信息,造成信息公開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罰款或者單項罰款。上海刑事律師帶您了解相關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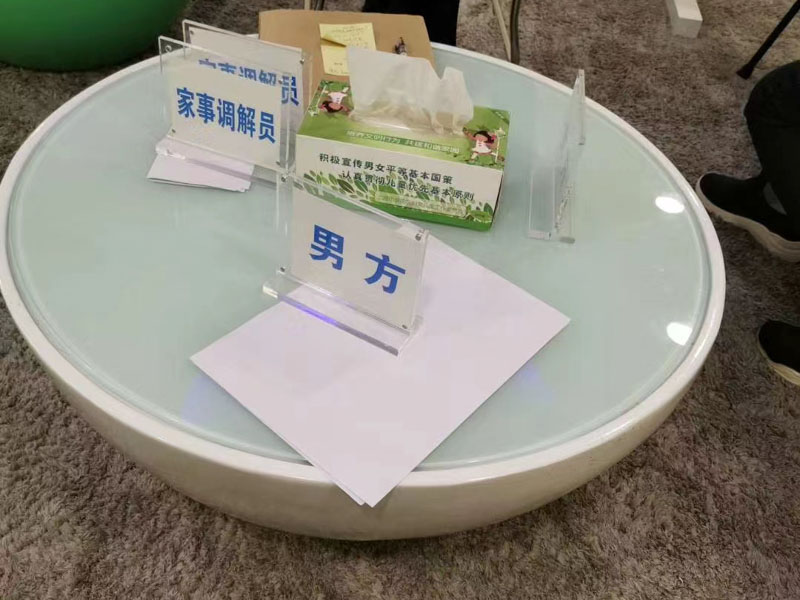
就其立法技術而言,至少在形式上,無論是侵權行為的主體還是侵權行為的客體,都得到了平等對待。考慮到司法官員有更多的機會和可能披露不應公開的信息,并考慮到第308條第1款首先將司法官員列為犯罪主體,以避免誤解該條款仍主要針對人權維護者、訴訟代理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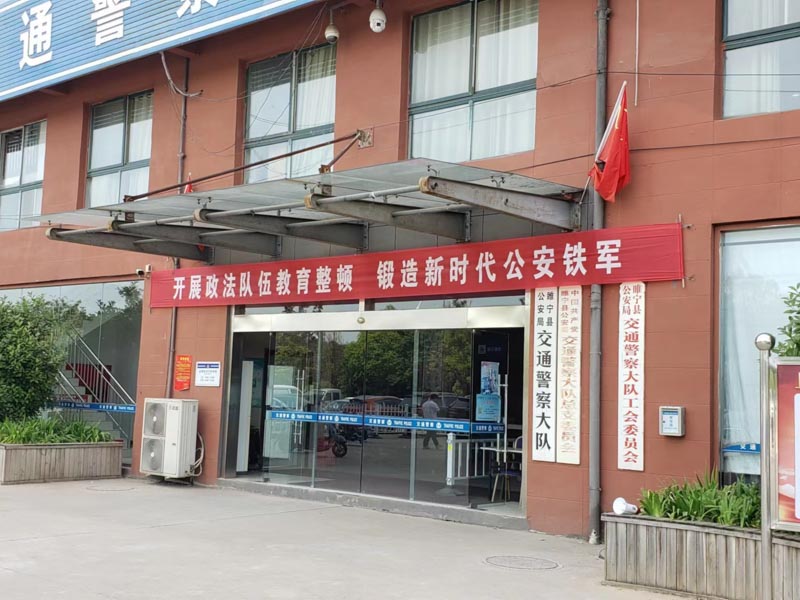
草案的上述規定,至少就其立法技術而言,將律師視為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建構者,而非異見者。作為異己,意味著律師總是作為消解、破壞、顛覆司法權的主體出現,所以迫使司法權必須時刻警惕律師的言行;意味著在法治權威的構建過程中,律師與包括法官、檢察官在內的其他司法工作人員背道而馳或相互對抗,從而忽略了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責任背景下共同努力實現法治的普遍目標。
作為建構者,意味著律師平等參與法治建設。雖然他們有不同的職能和責任,但他們與專業團體的其他成員有著共同建設、促進和改善法治的相同使命。作為異見者,律師被視為敵人;作為建設者,律師被當作同事。后者不言而喻,逐漸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共識。
不過,在我們贊賞《草案》在立法信息技術發展方面將律師作為一個法治社會建構者而非異見者的進步同時,我們國家仍然必須能夠看到《草案》中仍然存在著似是而非的立法研究問題,說明了中國這樣學生一種管理理念的轉變仍然是痛苦的、不情愿的,因而他們對于律師而言,這一教學過程仍然可能是艱難的。
在對立法平等待遇的思考中,除了上述無正當理由的無特殊待遇原則,即無身份者的無特殊待遇原則外,還需要考察無身份犯罪的成立是否與有特定身份者具有隱性相關性。也就是說,雖然它是一種無身份犯罪,但由于構成要件的確立和制度的安排,使得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口更容易違反規范,這意味著該規定的設立具有隱性的針對性。
這方面的例子包括草案第308條一款和《刑法典》第309條。前者規定,司法人員、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或者其他訴訟當事人披露不應當公開的信息,對于未依法開庭審理、造成信息公開傳播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行為,應當確定為犯罪。《刑事訴訟程序條例》訂明擾亂法庭秩序罪的構成要件,包括“襲擊司法人員或訴訟參與者; 侮辱、誹謗、威脅司法人員或訴訟參與者,不聽從法庭的勸阻”。
當然,也不排除上述犯罪中有司法工作人員泄露相關信息。但是,考慮到律師參與社會經濟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以及司法工作人員職能的相對封閉性和律師工作的相對開放性,可以想象,在實踐中,律師會比司法工作人員更多地犯這個罪。
同樣,我們也可以想象司法工作人員毆打訴訟參與人的罕見案例,尤其是司法工作人員侮辱、誹謗、威脅訴訟參與人以及其他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行為。但實踐經驗充分證明,就現有擾亂法庭秩序行為而言,幾乎從未審理過法院認定司法工作人員構成擾亂法庭秩序罪的案件。因此,上述規定都具有隱含的針對性,可能主要影響律師的執業行為。
基于這種無形的、有針對性的前提,我們必須考慮刑法是否真的將律師視為司法公正的建設者,還是仍然將律師視為異見者。而且,正是基于這樣一個前提,我們必須更加仔細地考慮刑法對律師執業的規制是否過度,是否存在濫用的風險。
對于過分,從謙抑性的角度來看,刑法應當堅持補充性原則,即只有在一般部門法不能充分保護某種法益的情況下,才應當受到刑法的保護,只有在一般部門法不足以制止有害行為的情況下,才應當受到刑法的禁止。

上海刑事律師認為,刑罰的邊界應該是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刑罰應該是國家為了完成保護合法利益和維護秩序的任務而不得不采取的最后手段,當其他手段也可以達到維護公共生活的社會秩序和保護社會和個人的合法利益的目的時,就必須放棄刑罰的手段。











 網站首頁
網站首頁  在線咨詢
在線咨詢  電話咨詢
電話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