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職務上的方便”是職務侵占罪必備的行動要件,通說對該罪持“繁多法益論”的態度,僅僅存眷財富權益,缺失從本質說明論上驗證對單元大眾權利法益的侵占,造成對其誤會和誤判。嘉定刑事律師告訴您相關的情況是怎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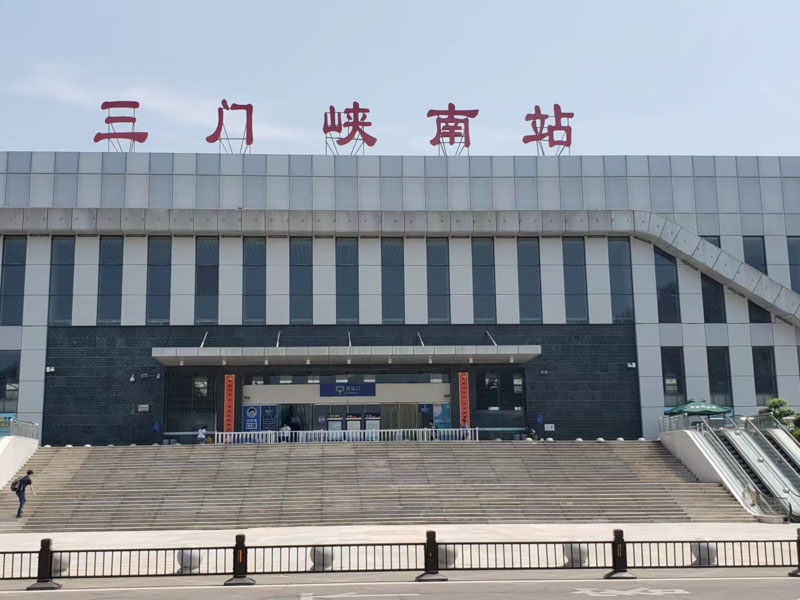
應在兩重法益的指示和限制下對其作實質的解讀和細致的框定,“職務”范圍的認定標準是從事具有控制、支配單位財產地位的事務,“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實質內涵是利用因承擔有關事務所具有的控制、支配單位財產的地位。
犯法的本質客體,即法益,擁有作為犯法組成要件說明目的的性能。其說明性能表現為對組成要件懂得的偏向和水平都受制于法益的內容,據此,對詳細犯法的本質客體,即法益的懂得與掌控間接影響組成要件因素的懂得與認定。
對于職務侵占罪的犯法客體,海內通暢的刑法教科書將其表述為“本罪的客體,是公司、企業或其余單元的財物所有權”,一些有影響的工具書和其余論著也持異樣觀念,是為通說。明顯,學界將該罪的客體界定為繁多法益——財富權力,此種觀點即為“單一法益論”。
但是,“單一法益論”沒有揭示本罪的另一法益——單位公共權力法益,在理解本罪的行為要件時缺失對單位公共權力法益的考量,難免只從客觀外在的行為類別上界定“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范圍,造成司法的誤解和誤判。筆者將從刑法規范實質分析的角度對該問題略抒管見,以求教于方家。
依據我國《刑法》第271條的劃定,職務侵占罪是“公司、企業或許其余單元的職員,利用職務上的方便,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行動。可見,職務侵占罪包孕兩大要素:“侵犯財富”(“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和“應用職務”(“利用職務上的方便”)。
這兩個要素在犯法組成要件上有著怎么樣的定位呢?法律實踐中,對于“侵犯財富”,既理解為主觀方面的行動要件,也理解為客體要件。作為一個行動,是對財富工具的踴躍影響,作為犯法客體,則是對財富權力的損害。

對此并沒有不同。對于“應用職務”,在通說“繁多法益論”的視線下,因為論者將該罪的客體僅僅理解為對財富權力的侵占,故“應用職務”要素——“利用職務上的方便”,只屬于主觀方面的行動要件,而非客體要件。
無論在何種情況下,“繁多法益論”都不會從“應用職務”要素中解讀出另一個法益——職務的清廉性或許大眾權利的嚴肅性和有效性。由此造成“應用職務”要素——“利用職務上的方便”與犯法的本質客體(法益)擺脫,不足法益的指示和限制,也就無奈運用法益的說明機能對其作實質的解讀和細致的框定。
“單一法益論”者往往從客觀、外在的“職務”行為或方式進行分類,得出該罪的“職務”就是“主管”“經手”“管理”等具體權能,于是理論和司法實踐的通說認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就是“利用主管、管理、經手單位財物的便利條件”。
據此,司法認定中,如果判定行為人不屬于“主管”者、“經手”者、“管理”者,或其職務行為不屬于“主管”“經手”“管理”之一,則否定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這樣難免導致對部分侵犯單位財產權益和單位公共權力法益的職務侵占行為不適用職務侵占罪加以處罰。
其次,羅小兵實施了虛構一個事實進行騙取他人財物的客觀社會行為。羅小兵向被害人通過虛構了其在重慶有工程的事實,并以高利息為誘餌騙取了被害人的信任,將兩百多萬元的資金“借給”他。
被害人國家正是我們因為沒有受到羅小兵虛構經濟事實的欺騙,產生羅小兵有正當的投資發展途徑,能夠提高獲利并及時有效收回企業借款的錯誤思想認識,才甘冒違法活動犯罪的風險發生挪用公共管理財產給羅小兵使用。
如果羅小兵將資金的真實生活用途可以告知被害人,顯然對于被害人是不會將公款借給羅小兵用于還賬、賭博。因此,羅小兵實施了虛構歷史事實的行為,使被害人之間產生一種錯誤問題認識,從而達到騙取被害人的財物,其行為是否符合詐騙罪的客觀構成要件。

最后,嘉定刑事律師了解到,羅小兵的行為發展造成了204、31萬元的財物無法進行追回,其犯罪數額特別具有巨大,給公私財物造成了一個重大經濟損失,后果非常嚴重,應當可以依照《中華民族人民民主共和國國家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網站首頁
網站首頁  在線咨詢
在線咨詢  電話咨詢
電話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