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明標準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而是一個復(fù)雜、多層次的綜合系統(tǒng)。因此,有必要根據(jù)不同主體、不同層次設(shè)定不同的證明標準。一是根據(jù)證明主體的不同區(qū)別適用證明標準。上海刑事律師來講講有關(guān)的一些情況。

在刑事訴訟中,不僅僅只是控方承擔(dān)證明責(zé)任,在某些情況下被告人也要承擔(dān)一定的證明責(zé)任。這就需要對被告人承擔(dān)證明責(zé)任設(shè)定一個標準。對此,可借鑒英美法系關(guān)于不同證明主體適用不同證明標準的成熟做法,即對控方的有罪證明需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對被告方則采用“優(yōu)勢證明”的標準。
也就是說在被告人負有舉證責(zé)任的情況下,被告人不必證明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而只需達到“證據(jù)優(yōu)勢”的程度即可。很顯然,“優(yōu)勢證明”是比“排除合理懷疑”要求更低的證明標準,如此區(qū)別適用,是與無罪推定原則相一致的。
一般而言,對犯罪事實的全部構(gòu)成要素都需要證明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而“排除合理懷疑”是對“證據(jù)確實、充分”的解釋,故還應(yīng)將其作為證據(jù)充分性與確實性的衡量標準。從整體與局部的關(guān)系考慮,沒有對個別證據(jù)或者局部事實的“排除合理懷疑”,則對全案證據(jù)與案件整體事實的“排除合理懷疑”也就喪失了其前提基礎(chǔ)。
因此,“排除合理懷疑”并非僅僅適用于最終地對全案事實的綜合判斷,在對個別證據(jù)的確實性或局部事實的認定進行判斷時,同樣可以參照“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
此外,還有學(xué)者指出,“排除合理懷疑”的適用范圍還包括對合法性的判斷,且“排除合理懷疑”在非法證據(jù)排除程序中更為適用,排除程序本身性質(zhì)更適合“排疑”的消極方法。因為證明證據(jù)非法很難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而只要能夠?qū)ψC據(jù)合法性產(chǎn)生合理懷疑,相關(guān)證據(jù)就應(yīng)當(dāng)排除。
畢竟在刑事訴訟中,是由控方承擔(dān)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zé)任,而被告方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承擔(dān)一定的舉證責(zé)任。如果對被告方證明標準要求過高,就相當(dāng)于變相減輕了控方的證明責(zé)任。二是根據(jù)證明對象的不同區(qū)別適用證明標準。

在刑事訴訟中,證明對象既包括實體法方面的一些事實,也包括程序法方面的一些事實,既包括定罪事實也包括量刑事實,既包括對,被告人有利的事實也包括對被告人不利的事實。這些事實在整個案件中的地位、作用都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因而證明標準也不應(yīng)完全相同。
但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3條規(guī)定的“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準確地說是對案件實體法事實中定罪事實所要達到的證明標準,至于量刑事實和訴訟程序中的某些事實,比如,回避、強制措施、違反法定程序等則在立法中沒有明確規(guī)定。因此,有必要對現(xiàn)有立法進行適當(dāng)完善。其一,需要明確量刑事實所適用的證明標準。
一般而言,由于量刑事實屬于實體方面的事實,因此,一般應(yīng)適用十分嚴格的證明標準,即需要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但是,如果屬于減輕被告人刑罰的情節(jié)事實則進行自由說明即可,無需嚴格證明,即不需要通過嚴格的證據(jù)和嚴密的調(diào)查程序就可以得出的證明,這也符合當(dāng)前有利于被告的立法精神。
其二,作為程序法方面的某些事實,如回避、強制措施、訴訟期限、違反法定程序等,也只需達到自由證明的程度即可,無需嚴格證明。
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卻很難準確適用,因為它混淆了“排除合理懷疑”與“唯一結(jié)論”和“排除一切懷疑”的概念。因此,深入研究"排除合理懷疑"的內(nèi)涵,完善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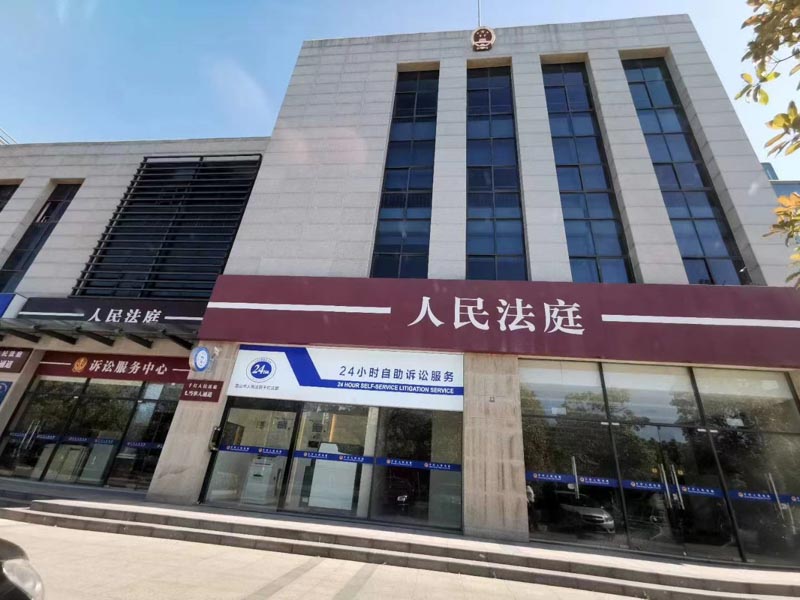
總之,上海刑事律師發(fā)現(xiàn),刑事訴訟證明標準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國刑事訴訟學(xué)界和司法實務(wù)界的熱點和難點問題。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規(guī)定了“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這對于進一步明確證明標準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功能。











 網(wǎng)站首頁
網(wǎng)站首頁  在線咨詢
在線咨詢  電話咨詢
電話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