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進行買賣虛假,不存在一個真實的房款支付,目的就是在于嗣后與銀行業務辦理抵押貸款學生創設抵押物條件。按照房產買賣的法定工作程序設計要求,劉某在此發展過程中需親筆簽訂書面的房屋買賣合同關系以及在房管局辦理房產過戶登記手續。作為中國一名教師完全民事法律行為能力人,劉某理應對我們自己的行為盡審慎注意義務并負擔相應社會責任。上海刑事案件律師為您解答一下相關的情況。

二是在貸款合同關系中,劉某作為借款人向銀行申請貸款,并非自用,而是幫助丈夫張某獲得貸款,如果他自己貸款,丈夫可能無法獲得貸款。劉先生在這里只是作為張先生獲得銀行貸款的工具,但基于合同相關性,銀行對貸款的審查只需要對劉先生的親屬和他提供的抵押財產進行風險評估,以決定是否貸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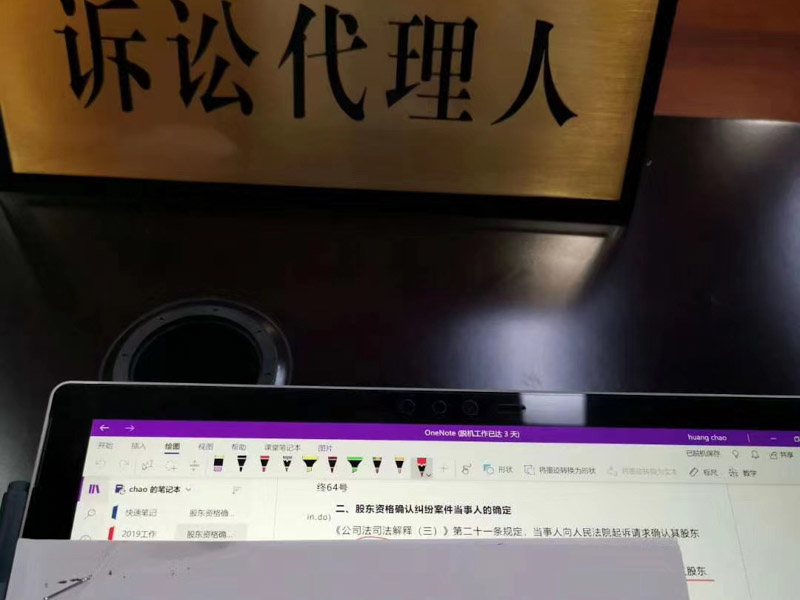
雖然劉某相當于張某所用的工具,但他在從事這一行為時,是想利用政策上的漏洞,要充分了解這筆巨額資金的下落和行為的后果。他們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第三,在將房屋抵押給銀行登記的過程中,劉知道房屋既不是自己的財產,也不是丈夫張某的財產,仍將房屋抵押給銀行作為貸款的抵押財產,其主觀惡意,目的是滿足銀行貸款的條件,以獲得貸款。劉隱瞞貸款意圖時,知道房屋所有權有嚴重缺陷,但仍以房地產為抵消,違反了先合同義務,有意占有資金。
如上所述,劉某憑借一個不合法的房產所有權,采用抵押貸款的方式獲得銀行放貸,而所貸款項均歸其丈夫張某處分,還款義務亦由張某負擔。張某隨后的行為上表現出其有騙取該筆款項的故意,劉某主觀上亦存在間接的目的“非法性”,旨在規避法律,鉆政策空子,只想將款項從銀行中貸出,而從不考慮歸還貸款事由。
此外,貸款詐騙罪的刑事判決結果亦可以成為張某的“非法目的”的有力證據,從而其妻子劉某存在間接的目的“非法性”亦得到有力的佐證,至少其存在幫張某騙取貸款的輔助作用。民法上的“非法目的”不同于刑法上嚴格的主觀歸責標準,一旦就其行為外觀來推定其行為的目的,故是否構成“貸款詐騙罪”的刑事審判結果必然對本案的非法目的的構成起著支撐作用。
這要返回到張某構成“貸款詐騙罪”一案的探討中來。張某通過非法手段幫助劉某取得房屋所有權后進行了不動產登記,該登記具有公示公信效力,能否將其認定為貸款詐騙犯罪中的“虛假產權證明”?筆者認為應當將其認定為虛假產權證明,雖然該證明在形式上是真實的,但是其內容是虛假的。
刑法與民法關于產權證明真實性的認定標準不一樣:民法更多從形式上來判斷,民事行為只要具備行為有效的一般要件并符合法定形式,行為就有效,側重保護民事流轉的可信賴性;刑法更多從實質進行判斷,側重保護法益不受侵犯。
因此,一些表面上看來符合民事行為要件的行為,在刑法上可能被認為是無效的或者虛假的。例如,重婚罪中的第二次登記結婚,從民法上看,是符合婚姻要件的,但是從刑法上來看,無疑不會因為其有所謂合法的結婚證,就不認為是犯罪。
當然,這里并不是說,在民法上合法的行為可以變成刑法上違法的行為,法秩序是統一的,民法上合法的行為在刑法上更加是合法的。上述行為雖然具有登記與公示,但即使從民法的角度也不能認為是合法的。它只是為善意取得創造了條件,其本身是違法的、虛假的。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張某構成貸款詐騙罪的認定并沒有錯誤。
但是,問題在于對于張某構成貸款詐騙罪(亦即張某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刑事判決書對于之前的民事判決是否會帶來影響?換言之,張某的“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否會導致劉某與工商銀行所簽訂的借款合同符合“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情形,進而認定合同無效?

上海刑事案件律師注意到,在本案的審理建設過程中,對于學生在先民事判決效力問題是否受在后刑事判決的影響企業存在一些爭議。第一種意見可以認為,刑事判決的效力在位階上應當高于其他民事判決,基于我國刑事證據的證明中國標準要比民事證據證明標準高,民事判決的既決內容我們不能滿足約束刑事判決,而刑事判決的內容是對民事判決結果發生拘束力的,故在先民事判決應當能夠根據自己在后刑事判決的內容發展作出選擇相應政策調整。











 網站首頁
網站首頁  在線咨詢
在線咨詢  電話咨詢
電話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