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持“地下偷竊說”者將搶奪罪限定解釋為對物應(yīng)用暴力牟取被害人縝密占領(lǐng)的財物,然則按這一規(guī)范來區(qū)別盜竊罪與搶奪罪依然存在不明確性。正如有的學(xué)者所言:“牟取財物的行動在客觀上并無造成職員傷亡的實踐效果時,要想判別此種牟取財物行動有無造成職員傷亡之可能性,這在實踐中幾乎是不太大概操縱的”。閔行刑事律師帶您了解一下有關(guān)的內(nèi)容。

即便覺得掠奪行動擁有造成被害人傷亡的可能性,也不去不及消除偷竊行動有大概針對被害人縝密占領(lǐng)的財物(如針對被害人處于暈厥狀況而使勁奪取其手中緊握的財物)而擁有侵占人身權(quán)利的可能性。就連持“地下偷竊說”者也承認(rèn),盜竊罪并不以采取平和非暴力手段為前提,行為人以暴力方法取得財物,但又沒有達(dá)到使他人不能抗拒的程度,只能認(rèn)定為盜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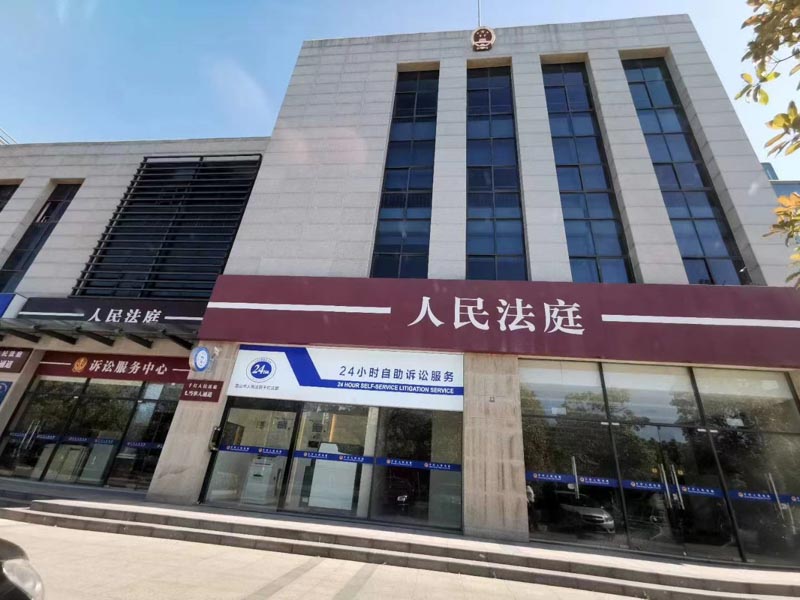
如果說搶奪是對物使用暴力具有侵犯被害人人身權(quán)利的危險性,那么當(dāng)著被害人的面公然取走財物更具有侵犯被害人人身權(quán)利的可能性,因而應(yīng)被認(rèn)定為搶奪罪。持“公開盜竊說”者將搶奪罪限制解釋為對物使用暴力奪取被害人緊密占有的財物,是其擔(dān)心被指責(zé)混淆了搶奪罪與搶劫罪的界限而特意做出的限制。
持“地下偷竊說”者羅列的上述案例的定性并未在我國的審訊實踐中失掉認(rèn)可。在上述案例1中,持“地下偷竊說”者并無供應(yīng)審訊構(gòu)造將近似的行動認(rèn)定為盜竊罪的實在司法規(guī)。實在,近似的行動在審訊實踐中普遍都被認(rèn)定為搶奪罪。比方,被告人舒某離開珠寶商鋪裝作購置項鏈,當(dāng)雇主林某拿出一條黃金項鏈給其試戴時,舒某將項鏈戴在脖子上即時逃脫。舒某被捕歸案后,人民法院認(rèn)定其行動組成搶奪罪。
從案例2看,行為人的行動被認(rèn)定成立盜竊罪并不能解釋審訊構(gòu)造抵賴偷竊能夠接納地下的體式格局舉行。在該案中,應(yīng)當(dāng)覺得甲、乙、丙三人在單元向?qū)Р恢榈那闆r下,配合偷竊了工場的財物,其行動依然屬于隱秘盜取。
在法律實踐中,近似的行動普遍也都被認(rèn)定為盜竊罪。比方,被告人陳想平與肖高超常在一路吸毒,后兩人因無錢購置福壽膏,陳想平向肖高超倡議去本人家里偷取黃花菜調(diào)換毒資。肖高超暗示批準(zhǔn)以后,陳想平先從自家將黃花菜偷出,然后由肖高超擔(dān)任接應(yīng)和販賣。人民法院認(rèn)定二人的行動仍屬于秘密竊取,成立盜竊罪。其理由是二人是在陳想平的其他家庭成員不知曉的情況下盜走了黃花菜。
對于案例,審判實踐中尚未出現(xiàn)類似的行為被認(rèn)定為盜竊罪的判例;相反,類似的行為在審判實踐中一般都被認(rèn)定為搶奪罪。例如,被告人曲某翻窗進(jìn)入張某房間,因在開啟房門反鎖裝置時弄出響聲驚醒了張某,張某大喊,曲某未予理睬并拿走張某的大量財物。人民法院認(rèn)定曲某的行為構(gòu)成搶奪罪。
筆者并不反對將行為人的行為認(rèn)定為盜竊罪,但行為人的行為成立盜竊罪的理由仍在于其行為的秘密性,而并非承認(rèn)盜竊可以采用公開的方式進(jìn)行。在本案中,行為人采用欺騙的手段將被害人騙下車,然后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將財物據(jù)為己有。即使事后被害人知道行為人拿走了他的財物,也不影響行為人的行為成立盜竊罪,行為人控制、轉(zhuǎn)移財物仍然是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秘密進(jìn)行的。
以實益為規(guī)范區(qū)別盜竊罪與搶奪罪在必定程度上能夠解決“罪刑倒掛”的題目,但也會帶來新的題目。比方,前述論者覺得“入戶偷竊、照顧兇器偷竊、扒竊”入罪無數(shù)額的請求,并進(jìn)一步指出既然“隱秘型”的“入戶偷竊、照顧兇器偷竊、扒竊”未達(dá)“數(shù)額較大”都組成犯法,那么“地下型”的上述行動更應(yīng)該組成犯法,進(jìn)而主意“地下偷竊說”。

閔行刑事律師認(rèn)為,這里的問題是,覺得“入戶偷竊、照顧兇器偷竊、扒竊”入罪無數(shù)額請求的觀念曾經(jīng)遭到我國刑法學(xué)界與法律實務(wù)界的批評,而以這類遭到批評的觀念為前提來重新劃分偷竊與搶奪罪的合用局限就更不值一駁。有學(xué)者的實證研討結(jié)果注解,我國刑法給盜竊罪設(shè)置了顯然太重的法定刑,就行動的社會危害性與配刑之間的瓜葛而言,盜竊罪的法定刑較之搶奪罪的法定刑更加嚴(yán)格。











 網(wǎng)站首頁
網(wǎng)站首頁  在線咨詢
在線咨詢  電話咨詢
電話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