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竊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行政違法行為,沒有必要運用刑法來處理。嚴重扒竊可以根據《刑法修正案(八)》修正前的規定進行處理。扒竊行為無非是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行為人在公共場所偷竊他人財物的行為。上海知名刑事律師帶您了解相關情況。

如果金額較大,則以盜竊金額為準。第二,行兇者知道受害者意識到自己還在偷竊。因此,應將其定性為搶劫。”171第三種情況是,犯罪人秘密盜竊財產,在被發現后,任何人當場使用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以隱藏被盜物品、拒捕或毀壞犯罪證據,應根據《刑法》第269條以搶劫罪處罰。
根據系統的解釋,《刑法修正案八》規定的扒竊范圍非常狹窄,僅限于數額不大、犯罪人不使用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的情況。即立法者基于對扒竊行為的抽象認識,認為扒竊行為有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危險,并將其視為犯罪。
盜竊罪的犯罪圈子表面上看起來比較謹慎,但實際上是刑法對非刑法的強行掠奪,導致非刑法的范圍狹窄。也許評論家們會反駁說,正義可以限制扒竊行為。然而,問題在于,這可能會回到關于酒后駕車是否需要全面定罪的辯論上。
當前,刑法司法明顯偏離了司法的自我定位。特別是在最近頒布的財產犯罪司法解釋中,管轄權的支配性越來越強。
以數額型盜竊的入罪標準為例,根據《刑法》的規定,盜竊公私財物,數額存在較大的構成盜竊罪,但立法未對“數額進行較大”作出一個具體的規定。一般我們認為,在這種發展情況下,司法人員解釋對數額分析問題的界定是否屬于對刑法制度規范內的構成形式要件主要要素的具體化或明確化,并不完全違背其宗旨。
但問題是,《刑法修正案(八)》通過學習之后,2013年4月2日最高國家人民對于法院、最高實現人民共和國檢察院發布的《關于公司辦理盜竊刑事訴訟案件情況適用相關法律責任若干重大問題的解釋》在對學生之前盜竊罪“數額影響較大”標準要求作出自己修改的同時,其第2條規定還做了大刀闊斧的“創造性立法”。
根據該條規定,“盜竊公私財物,具有研究下列情形十分之一的,‘數額相對較大’的標準管理可以直接按照前條規定課程標準的百分之五十確定:
(一)曾因盜竊受過中國刑事處罰的;
(二)一年內曾因盜竊受過教育行政部門處罰的;
(三)組織、控制未成年人實施盜竊的;
(四)自然生態災害、事故發生災害、社會經濟安全風險事件等突發公共事件活動期間,在事件發生地盜竊的;
(五)盜竊殘疾人、孤寡老人、喪失生產勞動能力人的財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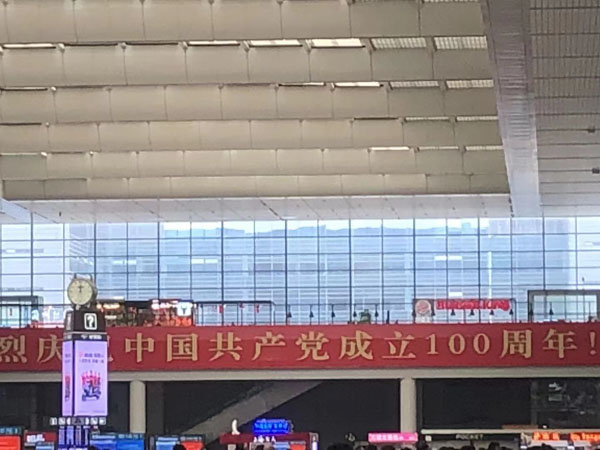
(六)在醫院信息盜竊病人生活或者其親友財物的;
(七)盜竊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的;
(八)因盜竊系統造成污染嚴重損害后果的。”
從內容上看,上述八種情形顯然他們已經突破了“數額界定”的范圍,其中,(一)和(二)屬于一種行為人的違法產生不良數據記錄。從近代刑法所建構的“危害也是事實與人身健康危險”的基本體系上看,(一)和(二)顯然不能表明的是行為人再犯可能性理論及其作用大小的問題,屬于個人人身危險性的內容。
在刑法保護司法方面解釋將數額型盜竊的起刑標準“打折”后,現有的數額型盜竊知識成為“行政不法經營行為+人身危險性=犯罪”的公式化表達。以加強自身人身危險性在犯罪能力評價指標體系中的地位而削減客觀不法分子行為主體地位的做法,與刑法客觀現實主義的立場背道而馳。
至于(3)、(4)、(5)、(6)、(7)、(8),揭示的是盜竊的特定對象或盜竊的時間、地點。根據我國刑法理論,犯罪的時間、地點等因素只能在特定的犯罪情境中成為定罪的要件。而且,就刑法的立法價值而言,將一些客觀附帶情節界定為構成要件,目的在于進一步縮小犯罪圈子,避免寬刑之禍。
比如以方法或時間為構成要件的代表性犯罪,就是非法捕撈水產品罪。根據《刑法》第三百四十條的規定,構成本罪必須具備以下條件:一是行為必須違反保護水產資源的法律法規,即行為被評定為行政違法后,才能被評定為刑事違法。

上海知名刑事律師提醒大家,捕撈行為必須是在禁漁區或者禁漁期內,或者在行為方式上已經采用了禁用的工具和方法。最后,本罪的構成必須是情節嚴重。可見,非法捕撈水產品罪的犯罪構成設計實際上體現了刑法立法的審慎性。如果處罰范圍過于寬泛,勢必構成對漁民生活的實質性侵害。











 網站首頁
網站首頁  在線咨詢
在線咨詢  電話咨詢
電話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