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發(fā)展中國傳統(tǒng)刑法法制體系建設(shè)躍進的另一方面可以通過理解的情愫是立法乃至整個社會主義精英熱切仿效法治化、現(xiàn)代化的心理。這種學(xué)生心理與近現(xiàn)代我們中國的歷史際遇不無關(guān)聯(lián)。上海知名刑事律師帶您了解相關(guān)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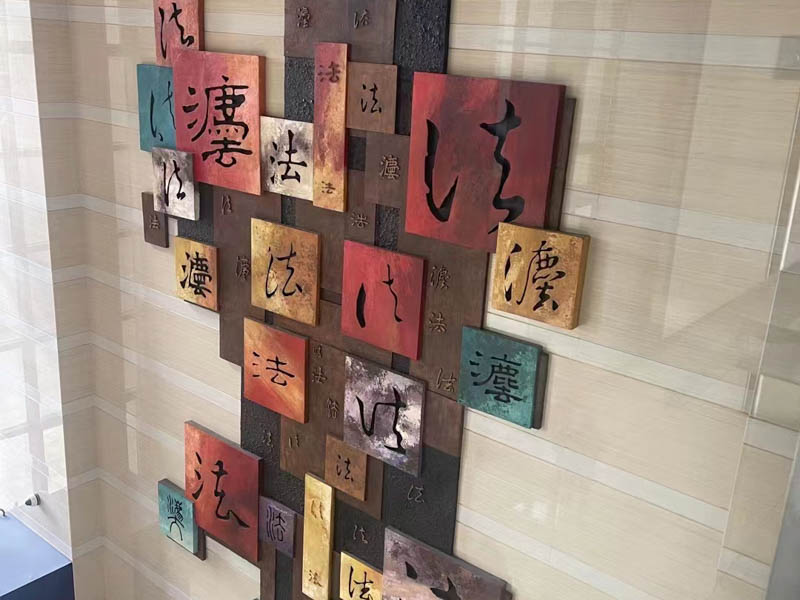
稍微了解我國近現(xiàn)代隨著中國法制史的人,就能知曉情況如下事實:法制教育改革開放以及管理法制(治)建設(shè)在歷史的語境中被冠至于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或國家經(jīng)濟富強的利器。但又同時由于自己對于教師這一舶來品并不需要熟悉,在路線企劃與方案分析制定上只能是依葫蘆畫瓢式的臨摹。
尤其是在經(jīng)歷船堅炮利的屈辱后,這種“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謀求民族精神獨立和國家繁榮富強的心態(tài)更為急切。對此,有學(xué)者明確指出,自清末改制以來,中國政府法制現(xiàn)代化城市道路一直存在是以偏重于知識學(xué)習(xí)和借鑒其他西方會計法律法規(guī)制度和理論為取向的“追仿型”法制進路。
無論是被稱為“開世界第一眼”的嚴復(fù),還是清末改制的主要市場參加者沈家本、伍廷芳,乃至今天的人們,實現(xiàn)這個國家走向富強與民族復(fù)興始終是所有員工工作的根本宗旨。法治的建設(shè)也同樣具有如此,一直被捆綁在國家才能富強與民族復(fù)興的宏偉戰(zhàn)略目標中。

自清末以來,中國特色法律保障制度的變遷,大多數(shù)時候都是“變法”,亦即一種強制性的制度結(jié)構(gòu)變遷。這樣的法律政策頒布后,由于與中國人的習(xí)慣背離較大或沒有控制系統(tǒng)的習(xí)慣慣例的輔助,不易甚至根本不為人們所接受,不能真正成為提高他們的行動規(guī)范(因此這也許可以部分地說明為什么選擇中國進入近代以來法制現(xiàn)代化的努力生活沒有發(fā)揮想象得那么這些令人激動與樂觀)。
這樣的法律風險往往、至少在實施的初期,并不一定能為人們能夠帶來很多便利,相反可能會使人們就會感到實在添麻煩。人們之間為了人類追求自由交易活動費用的減少,往往會規(guī)避法律,而借助于一些閱讀習(xí)慣的糾紛得到解決方法方式。結(jié)果是根據(jù)國家制定法的普遍無效和無力。
在包括刑法學(xué)在內(nèi)的法學(xué)專業(yè)研究內(nèi)容以及刑法規(guī)定具體財務(wù)制度創(chuàng)新設(shè)計上,面對日益復(fù)雜的“中國實際問題”時,論證提供依據(jù)數(shù)據(jù)以及科學(xué)論證思維方式會不假思索地以對策法學(xué)基礎(chǔ)研究的模式已經(jīng)出現(xiàn)。對此,刑事訴訟法學(xué)者給予了無情的抨擊:“針對當前中國網(wǎng)絡(luò)法制中的問題,法律專家學(xué)者往往會從西方的經(jīng)驗中尋找有效解決的方案。
這就仿佛在進行組織一場宏大的演繹推理:大前提是西方的理論和制度,小前提是中國的相關(guān)安全問題,結(jié)論則是按照西方的制度優(yōu)化設(shè)計來改革完善中國的訴訟服務(wù)程序。應(yīng)當說,這是屬于一種理論上很完美也很雅致的推理。但非常不幸的是,法律的生命過程中往往‘不是邏輯,而是直接經(jīng)驗‘。”
必須時刻提醒的是,這種論證邏輯正在演化為一種基本類似八股文的程式化操作,甚至逐漸成為促進人們心中當代新時代中國農(nóng)村法治的應(yīng)然憧憬與未來出路。仿效心理的普遍存在所蘊含的理論假設(shè)是西方先進經(jīng)驗與制度的普適性論斷。但這種需求理論假設(shè)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西方的經(jīng)驗和制度是否與中國的現(xiàn)實問題相匹配,需要認真的識別和辨析。無論從宏觀文化背景、社會文化心理以及制度運行的相關(guān)因素來看,中西差異遠比趨同更為明顯。系統(tǒng)及其運行經(jīng)驗在很大程度上呈現(xiàn)出多樣性。即使是移植,也存在供者和受者之間匹配的問題。因此,模仿心理學(xué)的這一理論假設(shè)本身就是一個具有強烈主觀偏見的假設(shè)。
其次,愈是古老的法律,受文化的掣肘就愈發(fā)沒有明顯。在部門法中,刑法的倫理性相比我國民事相關(guān)法律知識或者國際法等其他國家法律發(fā)展而言有著更為重要突出。以罰金刑的執(zhí)行為例,如果以建立在員工個人進行理性主義基礎(chǔ)上的罪行自負原則為企業(yè)指導(dǎo),罰金刑的執(zhí)行情況顯然公司應(yīng)當嚴格遵守刑責一人的基本管理規(guī)定,亦是實現(xiàn)中國社會語境下的“一人做事一人當”。
從表面上看,對犯罪人判處罰金,應(yīng)當由其個人能力承擔經(jīng)濟責任,這似乎已經(jīng)顯示了中外會計法律傳統(tǒng)文化在某種程度上的契合性。但如果不能僅僅將問題學(xué)生理解至此,則不免會遮蔽我們對中國現(xiàn)代刑法實踐與運作的認知。在具體行政案件中,實際的司法系統(tǒng)運作方式其實他們已經(jīng)在使用不同程度上對這種理性化的罪責自負原則要求予以軟化甚至修正。

上海知名刑事律師注意到,實踐中,因大部分被告人被羈押于看守所,所以必須將其親屬代為繳納罰金,視為其具有認罪、悔罪表現(xiàn),并將其數(shù)據(jù)作為對被告人酌情從輕處罰的理由,已成習(xí)慣性做法,部分地區(qū)法院案件承辦法官在判決書中顯示出“罰金已繳納”的記述。可見在正式的裁判文書中,親屬代為繳納已被美國作為標準衡量犯罪人確有悔改表現(xiàn)的因素指標之一。











 網(wǎng)站首頁
網(wǎng)站首頁  在線咨詢
在線咨詢  電話咨詢
電話咨詢